- 时间:
2025-11-18 - 作者:
- 来源: CNSO
| 在指挥家水蓝的带领下,中国交响乐团的2025/26音乐季以“北欧之光”之名,安排了体量超出常规的北欧交响乐作品,其中不少都是鲜少在国内演出的冷门杰作。10月31日,这个系列名下的第一场音乐会由水蓝亲自坐镇,带来了芬兰作曲家让·西贝柳斯的《降E大调第五交响曲》。而在音乐会上半场,享誉世界的英国钢琴家斯蒂芬·霍夫演奏了自己的拿手好戏——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d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尽管各自活跃的年代相距半个多世纪,又身处在不同的地理与文化环境,但是西贝柳斯和勃拉姆斯这两位作曲家拥有相似的音乐观:他们都选择了以严谨的逻辑和圆熟的笔触作为交响乐的追求。勃拉姆斯这部诞生于1859年年初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虽然经常以宏大和外向而著称,配器上却只用到了更加贴近古典时期的双管编制乐团,甚至没有加入长号。西贝柳斯创作和修订《第五交响曲》时,20世纪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十年,但这部公认具有大气魄的交响曲实际配器仍然仅有双管编制为基础的交响乐团,既不包括大号,也没有除了定音鼓以外的其他打击乐器。摄人心魄的音响质感全都来自对于这些既有声部的开发以及声部之间关系的调配,因此更加考验指挥家的指挥和乐团在细节上的完成度。 1907年,古斯塔夫·马勒前往芬兰赫尔辛基指挥巡演,其间西贝柳斯与他一同散步,并且留下了那段经典的对话。当西贝柳斯表示,交响乐更重要的是“交响乐的严肃、风格以及建立在主题之间内在的深刻逻辑”,马勒的回应则是,“交响乐必须像是整个世界,它必须包容一切。”事实上,西贝柳斯并非没有如马勒所追求的那样“包罗万象”的作品,《库勒沃》交响曲便是力证;马勒也远非不重视交响乐的逻辑性和严谨性,个人的音乐语言和风格更是极具辨识度。但是从这番对话中仍然不难看出,两位大师级作曲家各自更加关注的主要矛盾。 在浪漫主义音乐的大潮之上,与同时代的瓦格纳等作曲家相对比,勃拉姆斯的音乐美学几乎已经无需过多赘述。从这个角度上也就不难理解他对比自己年轻三十岁的西贝柳斯的赏识——1890年在维也纳会面后,勃拉姆斯郑重表示,“有朝一日他将成为重要人物。” 众所周知,勃拉姆斯曾二十年磨一剑地创作自己的第一部交响曲。《第一钢琴协奏曲》也是这个过程之中的产物,历经了从双钢琴奏鸣曲到交响曲直到最终成为钢琴协奏曲的构思演变。对此,指挥家水蓝和钢琴家斯蒂芬·霍夫都没有把这部作品简单地看作是一部“浪漫主义钢琴协奏曲”,也没有落入诸如“带有钢琴的交响曲”一类说辞的窠臼。他们共同试图达到的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互动境界,主要体现为外向而不失内省、对话而不失自我、立体而不失细节。 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篇幅格外宏大,几乎占到了整部作品一半的篇幅,但是只标注了“庄严地”(Maestoso)这一格外简洁的记号。这实际上为指挥家、钢琴家和乐团的演奏都提供了开阔的想象空间。在音乐会前几天的导赏活动中,斯蒂芬·霍夫也参与其中,是为这次活动的一大惊喜。他在活动的后半段加入进来,此前五分钟低调地来到门口准备。谈及勃拉姆斯这个乐章的开篇,霍夫幽默地以此作比:“起初是一段长长的乐团合奏,钢琴家只是坐在那里张望,之后则会以最优美的方式登场。但它不像很多协奏曲,钢琴一进来就是高调的姿态;而是像我刚刚进入这个场地时那样,你们的对话已经在进行之中,我不动声色地加入,但又给讨论内容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  当中国交响乐团在水蓝的指挥下开始演奏这部协奏曲令人印象深刻的乐队引子部分,霍夫一如既往地向左侧转身面向乐团。事实上,在此之后的整部作品里,每次到了乐团较长的合奏部分,他也会设法从琴键上抽身出来倾听。在水蓝精准挥动的指挥棒下,定音鼓的滚奏引导乐团建立起“庄严”一词的具体形象。先下行再上行的句子走向在弦乐声部手中具有明确的方向性,管乐提供的和声支持更体现了高级的品位,这种对于细节的讲究恰恰揭示了勃拉姆斯的作曲精髓。虽然起初的声音略微有些发紧,但舞台上的音乐家们很快就把状态调整过来。无论是铺就底色的低音提琴还是合而为一的长笛与双簧管,整个乐团逐渐成为真正有机的整体,沿着作曲家铺设好的路径顺理成章地将音乐推进下去。正是在这样的基调之上,小提琴每次大胆抛出的冲刺般的弧线得以更加出彩。 乐团演奏的引子过后,霍夫所说“新的东西”实为钢琴对于音乐原有调性的改变。从d小调转入D大调,他借助触键和踏板赋予了钢琴以温暖的色泽。但这种内省的声音同时留有发展的线头,随着乐团重新掀起风暴般的音浪,霍夫也顺势在琴键上挥洒了更多的能量。这种外向和内省的转捩在随后的整个乐章里多次上演,字里行间尽显展现出两位大师级音乐家之间的熟稔。比起渲染悲剧性的黑暗气氛,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留给了音乐背后美与深情的一面。具有圣咏气质的第二主题先是在霍夫的手中以优雅的声音亮相,左右手之间的对位关系成为了牵动人们内心想象的引线。而在这个主题的素材陆续交给乐团各个声部来完成时,水蓝带领中国交响乐团营造出如梦似幻的氛围,特邀圆号首席韩小光充分利用了这件乐器的声音可能,先是拿出中气十足的声音、随后又让圆号化为极致温柔的弱奏,呈现出同一组跳跃的音符的不同性格。乐团几位木管首席在时而接续、时而重叠的演奏中相互交融且熨贴的声音,显然经过了细致而有效的排练打磨。 正如霍夫和水蓝所言,《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承载了勃拉姆斯对于舒曼一家的多重情愫。深情无疑是这段音乐的底色,但它同样不乏缅怀与纪念。这个乐章再次以乐团的合奏段落开篇,国交乐队在经过了第一乐章的洗礼后状态更盛,弦乐的织体演化连同大管和圆号等乐器附着其上的对位旋律完全可以用美轮美奂来形容,各个声部的音乐家们在水蓝的领衔之下表现出了罕见的细腻与平衡。水蓝和霍夫都没有把乐团仅仅当作是烘托气氛的角色,不仅前者精细设计了乐团部分的每个句子以及和声的走向,后者也让手中的钢琴与乐团形成了室内乐般的对话关系。中段不同寻常的和声色彩将人带入了另一种声音世界,霍夫此时的角色就像是篮球场上的“组织前锋”:一面在幕后推动木管演奏楚楚动人的乐思,一面在转瞬之间引出乐团如同潮水般的小高潮,另一面也在这些片段之间完成自己的亮相。在此期间,单簧管和双簧管首席都有高光演奏,仅用朴素的线条就让人们感觉到身处音乐的温暖怀抱之中。  与前两个乐章相比,第三乐章终于从钢琴开始,霍夫用优美的跑动和澎湃的能量,为这个乐章的回旋曲主题奠定了基调。在回旋曲的各个段落衔接处,水蓝和霍夫都做了清晰而精细的构思:第一次A段转入B段时,小提琴的句子形态如同送出了邀请,将F大调洋溢着热情的旋律请了进来。转回A段时,具有突然性的圆号和随后的小号干脆利落,但在此前弦乐已经铺垫了先声。第二次A段转入C段,圆号的和声转换既是对于过渡段的填补,又起到了对于乐团的承托作用。降B大调上宽厚温情的旋律同钢琴在反拍上的句子相映成趣,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在圆号复述钢琴旋律后的赋格段。实际上,从当晚第一乐章开始,水蓝带领的国交乐队每次遇到复调段落都胸有成竹,总有令人信服且印象深刻的演奏。第三乐章C段的这处赋格以第二小提琴为起始,穿插引入低音与中音后,第一小提琴最后加入。得益于乐团客座首席陆威、特邀二提琴首席周启等人的坐镇和带领,加之他们自己多年来的合作默契,即使在两个小提琴声部对称布局的乐团摆位中,国交的弦乐依然呈现出了工整明晰的复调逻辑。  回旋曲的尾声(Coda)也是整个上半场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段落,尤其是当弦乐最后一次以复调的方式激发起整部作品的高潮时,乐团各个声部的演奏规格、相互之间的协作关系、钢琴与乐团的合拍以及钢琴自己的演奏发挥全部达到了最佳状态。只见水蓝积极地调动乐团制造出递进式的动态,霍夫恣意在键盘上挥洒乐思,但每个切面上钢琴和乐团都合在拍上、融在心中,最终的“高潮”远不止于音响上的刺激,更会让人有感于由内而外的动力和激情。 一曲恢弘而艰深的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结束后,霍夫顺应观众的呼声又回到了舞台之上,加演了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作品9之二》。这首夜曲对于他来说可谓信手拈来,基本是返场的常备曲目。肖邦音乐中令人津津乐道但又捉摸不透的“诗意”,在霍夫这位钢琴家兼作曲家兼作家的手中仿佛顺理成章就能实现,背后则是对于自由节奏的成熟设计和对和声走向的精准把控。而在这场音乐会上,霍夫加演这首夜曲似乎还有一层特殊的效果——下半场的西贝柳斯《第五交响曲》就是降E大调,上半场最后的余韵也算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交响曲的预告。  音乐会下半场,备受瞩目的“水蓝指挥西贝柳斯”终于亮相。多年以来,水蓝演绎的北欧交响乐作品有口皆碑,这一方面自然离不开他本人在北欧多年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另一方面更本质的原因当属他一如既往深入音乐本身的研究与见解。不仅如此,水蓝长期以来着重强调音乐流动和呼吸的艺术风格,与西贝柳斯的作品在内在气质上更是相得益彰,因此每次这样的现场都令人尤为期待。   在经年累月的演出实践和建设乐团的经验中,水蓝练就了一种特殊的本领——他很会冒险,善于利用直觉,甚至是在一定尺度内牺牲些许的“准确”,但是不会在他最看重的核心概念上妥协。比起四平八稳的工作方式,这样能有更多机会实现极致的音乐呈现,但又注定要面对更高的“风险”。因此,这种艺术目标的落地极为考验一支乐团的客观素质,但在这一基础上更加重要的是其实是乐团与指挥家之间的默契与信任。 自从水蓝2024年1月重返中国交响乐团的音乐季、2024年7月正式走马上任乐团艺术指导至今,这场西贝柳斯《第五交响曲》是他执棒乐团排演的第9场音乐会。从音乐会的整体来看,尤其是下半场水蓝领衔演绎的这部西贝柳斯交响曲,应属两年来当之无愧效果最佳的一次现场。无论是乐团在技术上客观的完成度,还是在响应和贯彻指挥的意图,以及音乐会现场主观带给人的感染力等方面,这都是目前水蓝任内国交的巅峰之夜。   自从年初苏克《第二交响曲“死亡天使”》横空出世、四月份拉威尔《达芙妮与克洛埃》第二组曲技惊四座,到六月份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守正创新,再到此后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和理查·施特劳斯《堂吉诃德》巩固提高,这次的西贝柳斯《第五交响曲》很可能成为水蓝与今天的国交相互磨合以及开辟新篇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虽然这次乐团依然按照计划邀请了陆威、周启、韩小光等特邀首席前来助阵,但是弦乐的演奏质量追根溯源本就是由整个声部而非某一个人决定,管乐和打击乐等(包括这场音乐会并未涉及的部分乐器)各个声部近年来乐团逐步吸纳和培养的年轻音乐家已经能够担当重任和崭露头角。整部西贝柳斯《第五交响曲》就是当下乐团良好状态和高涨势头的写照。 站在笔者个人的视角来看,西贝柳斯的《第五交响曲》是一部充满特殊魔力的作品。它的篇幅不长,演奏时长算下来甚至只有音乐会上半场协奏曲的三分之二;但它自始至终都有一种吸引和牵动听众神经的巧劲,让人一听上去就欲罢不能。这背后蕴藏着内在的动力,仿佛制造出了某种磁场。凡是成功的演绎,都是能够令人体验到这种境界的演绎。 要想在西贝柳斯《第五交响曲》中达到这种境界,乐团需要把两件事做到极致:一是“水面之上”,二是“水面之下”。前者指的是那些负责“制造效果”的角色,往往体现在旋律之中;后者则是让这些效果得以被真正感知的角色,堪称是这部作品里的“扫地僧”,往往属于“不找就注意不到、仔细一找就会致命”的那一类,其中尤以弦乐最为典型。 《第五交响曲》甫一开篇,西贝柳斯让圆号率先演奏出来自远方的声音——从整部作品的第一个音符到最后一个音符,圆号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水蓝在这场音乐会上将圆号声部安排在了面向乐团的右后方,号口传出的声音得以音乐厅的墙壁之间形成更多次的反射。国交的圆号声部在刘一君与韩小光的共同坐镇之下,延续了上半场的出色状态,在整个交响曲都保持了高能量和高规格的音乐输出。这不是简单的音符正误和音准与否的问题,而是在声音上达成了指挥的追求。第三乐章的所谓“钟声”主题同样由圆号演奏。这个乐章素来被认为是在描绘天鹅飞翔的画面,弦乐干净凌厉的碎弓和定音鼓的滚奏像是天鹅起飞前快速蹬出的双腿和溅发的水花,随后圆号以三个音符为一组的旋律真的就像是从乐团里飘了起来,声音本就带有一种悬浮感,再加上抛物线式的动机走向,实在令人发自内心地击节称赞。  木管组在这个夜晚的演奏同样具有难能可贵的品质。尽管长笛声部起初音准有些偏低,但很快就自我调整了回来。在极其考验音准体系一致性和实际演奏准确性的第二乐章,场上的木管演奏员们圆满完成了每个变奏里细腻变化的音响。无论是在第一乐章素材延展还是第二乐章主题变奏的过程中,木管的句子常常是在纵向的空间里发展,彼此之间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声音图层,使得整个声场非常开阔。而在演奏具体的旋律时,各个声部的首席已经能够比较充分地对于水蓝的指挥意图心领神会——即便是寥寥几个音符组成的小句子或小动机,音符之间伸缩的尺度也总能让听懂的人会心一笑。 当然,西贝柳斯《第五交响曲》的“扫地僧”非弦乐莫属。正是他们需要在很多时候扮演生活中“阳光和空气”一般的角色,令人们受益而不觉、失之却难存。水蓝和弦乐声部想必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精雕细琢每种不同的声音形象究竟该如何掌握:当管乐声部演奏属于自己的高光瞬间时,往往都是弦乐在铺垫音乐的底色;在乐团色彩和气质转捩的地方,也都需要弦乐来引导和增色。从碎弓的音准、清晰度和整齐度,到线条的均匀与完整,再到植入进默认动作里的合奏意识,这些“基本要领”能否不打折扣地完成,构成了音乐效果的基石。第三乐章开头那段迅疾凌厉的颤音,国交的弦乐声部让每个音符都清晰可辨,几个声部线条在共同的运动之中既独立又统一;除了对称分布的两个小提琴声部多次拿出了亮眼的互动,中提琴声部的“芯”坚如磐石,低音提琴也在这个激进的运动中保持了极强的控制与灵活。而这一切又同乐章结尾铜管再次以放慢的速度奏出所谓“钟声”主题时,弦乐焕发出大气魄的线条形成了对比和呼应——起飞的姿态此时被翱翔的姿态取代,“震撼”不止来自于管乐带给人的直观刺激,更得益于管乐和弦乐在彼此一致的声音概念基础上带来的整体音场。 这一切不得不再次回到指挥家水蓝对于乐团声音和整体状态一如既往的追求。而在西贝柳斯交响曲的结构中,他更是极具智慧地找到了这位作曲家笔下严谨与松弛之间的平衡点。大的方面上,他牢牢掌控着素材由简入繁的逻辑和步调,毫不拖泥带水;但是到了关键时刻,最典型的例如第三乐章结尾,先积蓄再释放的能量则会一跃化为点睛之笔。这部交响曲前无古人的尾声由六个和弦构成,用水蓝的话来形容,表现的是一种见到奇观后“瞠目结舌”的反应。于是,西贝柳斯也让这个结尾成为了一片奇观。水蓝充分发挥了预期管理的艺术,几个和弦之间的休止时值也像一条弧线,制造预期张力的过程中每次都会“多给一点”和弦的织体层次,调配乐团在圆融的声音之中适当露出需要强调的声部。定音鼓先行的设计则为这片奇景增加了些许的确定性,也让乐团更容易把握方向——这在乐章开头定音鼓被强调的装饰音里面其实就已初见端倪。   值得感到庆幸的是,在这个多次出现休止的结尾,音乐会当晚的观众们全都屏息凝神,默契地等到了最后结束才给予热烈的掌声,没有人提前“擦枪走火”。这不仅在国内的音乐会现场,哪怕在海外也不是每次都能实现。最后一个和弦结束后爆发出的欢呼无疑证明,现场的所有人都被音乐和演奏所触动和感化。这当属是西贝柳斯作品在中国值得被铭记的演绎。 而在《第五交响曲》演奏完毕后,水蓝又带领中国交响乐团返场了同样来自西贝柳斯的《忧郁圆舞曲,作品44之一》。从选曲到演绎,这首精致而亲切的音乐都是大师手笔的体现,既延续了音响奇观的余韵,更将交响曲的气势轻轻卸下,带给人以温柔优美的更深遐想。 再由这场的西贝柳斯向整个乐季里的北欧音乐说开去,很多让我们爱不释手的西贝柳斯演绎,确实都来自芬兰或相关指挥家。但是仔细想想,真的存在某种“芬兰风格”吗?这场音乐会结束后,水蓝分享了一段轶事:在他担任哥本哈根爱乐乐团首席指挥期间,一次乐团在巡演中安排了西贝柳斯的《第五交响曲》,先后由两位指挥大师奥科·卡姆和列夫·赛格斯塔姆执棒。同为芬兰人和公认西贝柳斯专家的他们,对于结尾的那些和弦有着截然不同的诠释。卡姆的处理轻巧利落,赛格斯塔姆则是势大力沉,休止符的时值几乎是卡姆的两倍。事实上,“芬兰风格”也许有地道一说,但是并无唯一之法。这种音乐从乐谱到演奏的可能性,正是音乐的重要魅力。  撰稿:姜太行 责编:段梦 摄影:国之骄子 排版:陈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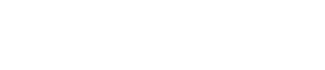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42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423号